梅钰,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,临汾市首届签约作家,作品发表于《山西文学》《黄河》《黄河文学》《海燕》等,曾获黄河文学奖,临汾市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等,著有小说集《十二个异相》。

一册《甘蔗》,读了放,放了读,因着琐碎杂事、各种应酬,本质里,是对文本的敬畏——瞄一眼,便窥见莫大空洞,提示自己浅薄,单有阅读的快感,无法明晰架构之妙、意趣之妙、言语之妙,更不能娴熟文中密布的铺设、埋伏,读过去几页,脑子乱了,如入迷宫,需要翻回去,重新拾捡漏下的某句某字。如高手对招,不能分神,心眼一岔,错过不止万水千山。
晋侯的厉害,我早晓得的,文字的驾驭者、操控者。最初听名,就说是文体全能,不论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专题片脚本,没有他不行的,是吃透了每个字的精髓,且能随形附意,拆分排列,重新赋予词语新意的。相当于张三丰自创太极,须把天下武功拆开了、拆散了,合并归类,一一克制,组合成拳。我看晋侯,总觉他毕生都在研学这门功课,万事让位给它,服务于它,它又回馈到万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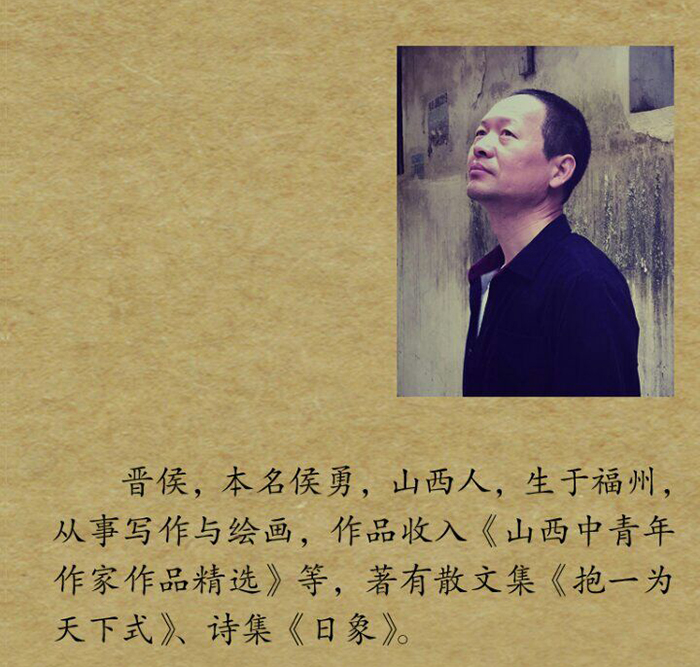
第一次见面,是七年前的冬日。酒是老酒,壶是陶壶,连碗,都是窑里直接拿下的,深褐色,有粗细不同的纹理。当时他住太原,公交车至“财大北校”,北行十几米,一座五层小楼。屋里全是书,架上搁不完,摞在桌上、沙发上、床上,几无下脚之处。人立于其中,总觉矮小。那时刚入圈,不懂文学需要广涉人学、社会学、伦理学、心理学,乃至建筑、宗教、民俗等等,看他的书五花八门,林林总总,像村级图书馆,心下不屑。他端碗豪饮,几碗下肚,大讲而特讲,从俄罗斯文学到拉丁美洲文学、日本文学,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、超现实主义,从马尔克斯到福克纳、普鲁斯特。开了我的眼。我的文学启蒙,真正始于那个冬日。同行三人,亦如我般醉心听,任他引领,遨游于广袤的文学圣殿。
自那以后,便关注晋侯。中学就显现出不俗的文学天份,和翼城同样优秀且知名的作家阎扶、朱宾自创文学期刊,出版的《1个2个3个》具有鲜明的辨识度,至今都是那年那月的文学潮流。本有一份极有前途的“正经”工作,说不要,便不要了,去太原漂。漂得非常高端,混出另一番天地,为了文学,又放弃了。后来通过图片,见他时而长发飘飘,时而光头熠熠,均飒飒的,自有一股我立天地间,任尔东南西北中的洒脱,有不同的风骨。
似乎明白了。
晋侯为文,不俗。《抱一为天下式》《日象》《甘蔗》,均不赘一词,读来疏朗,字间却隐有千言,要你自行辨别、添加、吸附,倘无此种本能,自是一片迷乱,不知他何出此言。况千头万绪,都隐在内里,不细品,不明他排布几何,明暗交替、融合中,场景变幻,人物出场,移形换影,移步换景,是变化的七十二阵图,行走的三十六计谋,是一出出精采的木偶戏,被他提线在手,由心排兵,随意布阵。
《甘蔗》为例,这个南方小镇的百年,是一条汹涌的河,故事一篓筐,人物几十代,个体与时代碰撞,生发出一重重的命运,在河里兀自沉浮。晋侯是优秀的打捞者,在时间与空间的交错中,敏捷地抓住一个,一层层铺设,一条条纠结,将“甘蔗”的百年拆分,将出场的人物分解、合并,让它们呼吸、脉动,让它们自己浮出历史的河来,云淡风清地叙述。晋侯告诉读者:我只是个忠实的记录者,那些曾发生的,正在发生的,即将发生的,有种种可能,种种走向,并不由我来操控,它们的归宿交由辽阔的命运。
十个短篇,十个故事,十个命题,十种情绪,以甘蔗为生发点,晋侯从百年的历史浑圆里取一点切入,横一刀,竖一刀,深一刀,浅一刀,切面上浮着历史的风尘与气泡,他用针尖戳破,细致观察,精准描摹,一层层剥出皮毛、肌理、骨水,乃至淡蓝色血管里流淌着的鲜红的血汁,百年甘蔗的由里及外,就在他一层层的切剥中渐次清晰、明朗。

总觉得,《甘蔗》隐在文本以外的东西远比呈现出来的更多,它的复杂性、包容性、简约性、多变性,总让人疑心晋侯写的不是小说集,而是好词好句集锦,随心情添词添句,就能有另外的可能。像糖精,添一杯水是一种味道,添两杯水是另外一种味道。
文如其人,晋侯为人,更加不俗。
因为老父身体有恙,他于是经常回临汾,先是一月一次,后来一月两次,三次,最后索性从太原搬回,随身一车书籍,并无俗物。我们已经相熟,混去翼城,在“寨上”点豆摘瓜,坐在连翘花底拍照,裙底飞起三五蝴蝶,一起去扑,他总是更洒落、更尽兴的那个。偶尔小聚,三五七八,吃吃喝喝谈谈,他也舒心,小醺后吟诗,或大谈而特谈,更高、更广、更深,有时我们跟不上,小斧子扬扬,把他拽回来。不一会儿,他又远了、高了、神了。
那时他初创《砍诗群》,每周“同题”,由他亲自操刀,线上授讲名诗佳作,点评诗友作品,谈到兴起,隔着屏幕都在眉飞色舞。线下,他过分低调,偶尔参加作协的文学活动,并不聒噪,淡淡的,细长身子隐在众里,若有若无。
他总在“行走”。说某天某日步行去翼的哪里,襄的哪里,侯的哪里,说哪一地的风从颜面吹过,让他想起哪一场的风,当时谁的环珮叮当,空响谁的欢歌与惆怅。有时同行,一车人叽喳,他又总在谁的一句话后思索到文学的多种可能。
我感觉,他一生遵从文学,一生又逆反着文学。喝酒、喝茶、刮痧,写字、画画、旅行,研究宗教、心理、中医文化,偶尔兴起,会唱民歌小调,调子悠长,像从远古刮来的一阵风,让人心里痒痒的,想发疯。
现在想到晋侯,总看到他长衣阔袖,游荡在闽江边,偶尔歌吟,只是将骨子里一口气顺掉。
他只顺从自己这口气。
所以,才有《甘蔗》!(梅钰)



- 黄河新闻网
- 黄河新闻网吕梁频道
- 山西省委社情民意通道








